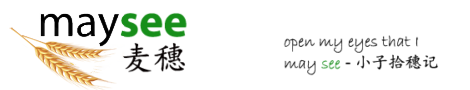美国和中国社会现状对比
最近看到一些文字和评论,论到有关中国政府体制的不合理性。这是一个极大的话题,很难综合评论,只能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就政府管理这一具体层面而言,从政府工作效率来看,尽管中国机构臃肿,其效率仍高于美国政府。
具体数据可以说明:中国政府明面上的财政税收约为18万亿元人民币(约2.8万亿美元),占GDP的15%;而美国各级政府的明面财政税收超过10万亿美元,占GDP的33%。
换言之,美国全社会的税收占比是中国的两倍以上(注意是占比,不是总数,所以更有可比性)。
在美国,领取政府薪水的工作人员接近2000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9(即每9个就业人员中有一人领取政府薪水),这一比例与中国大致相当。因此如果说政府机构臃肿,中美之间不分仲伯。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与中国相近,为何其财政税收占GDP的比例却超过中国两倍以上?超出的那一倍的钱都哪去了?(再次注意,因为这里说的是比例,所以跟 GDP水平、个人人均收入以及美元和人民币的底价没有任何关系。)
这里有好几个因素需要考虑到。
首先,上述数据仅指明面上的税收。实际上,中国经济和社会还承担着一种隐性的、表面不可见的税收——腐败。虽然缺乏精确估计,但若将腐败成本计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总体税负可能与美国相当,即约为GDP的1/3。
鉴于中国明面税收仅占GDP的15%,这意味着“腐败成本” 约占GDP的18%。但是注意这里的 “腐败” 是广义的也是概括性的,不仅仅包括平常大家所知道的官员贪污 (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包括各级政府浪费以及政府使用各种手段所榨取攫取的财富 (比如政府使用地产所赚的钱,在本质上属于这一类),等。
但无论如何,既然美国税收占GDP的比例是中国的两倍多,而政府雇员比例又相当,那么美国多的钱都花在哪里了?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关键:
美国政府的税收除了支付政府人员工资以及国防外,大部分用于各样社会福利;
而中国的政府税收(包括明面和隐性的),除支付公务人员工资和国防外,主要用于下面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再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性产业政策支持),二是腐败层面的消耗。
中国弊病
注意上面中国数据显示一个矛盾体,一个负面,一个正面。
腐败是负面,多害少利。这一点比较简单明确,在此不赘述。
政府投资是正面,但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政府所控制的投资在过去40年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红利,尤其是在基础建设方面,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不幸的是,过度强调国家整体发展和国际竞争力,导致中国经济难以突破 “投资驱动型经济”的桎梏,因其无法有效提升国内大众消费能力,也未能培育真正的中产阶级。这是经济学规律的必然结果。
这方面,懂得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包括 Michael Pettis 有极其透彻的论述。可惜中国社会,从政府高层到经济学界,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仅靠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就能实现经济的无限发展。但如今,这一因素的正面效应已大幅减弱,对中国大众未来生活的益处远不及过去40年。不仅如此,过去累计的投资现在越来越多由于入不敷出正在成为不断增加的经济负担。
同时,在早期发展时,大量民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人口红利,并且由于经济起点极低,即使是极低的工资,也对这些民工是极大的经济利益。但30年之后,当这批人的血汗被榨干以后,他们并没有富裕起来,没有成为一个类似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消费群体。他们不再是中国经济的驱动力,而是负担。
“国富民强” 是一个美丽的说法,但实现此目标不仅需要合理的制度,更需要整个社会的道德资本(moral capital)。 一个从国家政府到企业主过度贪心的社会,必然会对社会中低层深度剥削,所带来的最多只能是一个 “国强民穷” 的矛盾社会,而不是国富民强。
而相对之下,美国整体社会过去250年,尤其是1990年之前,比较均衡发达。虽然也有严重的贫富差别,但是却造就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这不仅和美国的政治制度有关,更重要的是与美国基督教价值观和文化有关。传统上,美国社会强调博爱并尊重人性和个人价值。这种社会环境不仅充分鼓励创新,也相对尊重大众劳动价值,因此是造就强大中产阶级的根本基础。
美国弊病
但是,反过来看,美国政府当今在个人社会福利上的巨额投入,其社会效益真的那么显著吗?
回顾美国历史,其制度优越性曾远超其他国家,这一点是事实。然而,这种优越性自上世纪70年代起迅速下降,原因在于美国文化的堕落。
文化堕落一方面表现为美国人变得愈发自私(并非比其他国家的人更自私,而是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明显越来越自私);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精英阶层的傲慢与腐败日益加剧。
这种腐败不是简单制度的腐败,而是人性的腐败。
比如,过去多年,美国每年平均浪费在无效的个人福利上的资金超过1万亿美元,疫情期间甚至一年超过5万亿美元。这些资金虽未被贪官侵吞,却在美国人的自私与傲慢腐败中被浪费,不仅未能为社会和经济带来益处,反而加速了美国社会文化的堕落。
总结
中美两个社会目前都处在极大的压力和危机之中,甚至都有崩溃的危险。起因并非简单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刻的原因:人性的败坏,即圣经所说的人的罪 (sin)。
在个人层面,无论哪个社会,罪的机制都是相同的,是从每个人人心里发出。但是在宏观层面,人的罪在不同的社会却会出现非常不同的运作机制。中国和美国就是典型的对照例子。现今时代,两个社会都被罪所侵害和腐败,唯一的区别是,在中美两个社会,其腐败的宏观病症和传播机制截然不同。
因此,断定哪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更优绝非一个简单问题。
不同社会和制度确实存在相对优劣之分。然而,美国建国初期,像华盛顿和富兰克林这样的先贤清楚认识到,政治体制只是人性(humanity)之树结出的果实,而健康人性的根基在于信仰——不是任何信仰,而是对创造世界之真神的信仰,其核心是 “道路、真理、生命”。
愿所有追寻真信仰——即道路、真理、生命——的人们,无论是美国人、中国人,还是全球所有人,都能早日觉醒。